佩里·安德森,1938年出生,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政論家。1962至1982、2000至2003年任《新左評論》主編。現(xiàn)為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學和社會學教授,《新左評論》編委會成員。
去年,安德森教授在上海接受了《上海書評》的專訪,現(xiàn)分三部分刊出。在訪談的第一部分,安德森教授談到了風格與形式、一般的方法與特殊的方法、霸權國與霸權體系、封建主義與絕對主義、儒家與法家。

佩里·安德森的著作,Kheya Bag攝于《新左評論》編輯部。
我想從風格談起。幾十年來,您的寫作風格受到了從左到右許多知識分子的褒譽:它明晰、透徹、淵博、雅致。我注意到,您似乎尤其偏愛“風格清晰”(clarity of style)、“形式簡潔”(economy of form)的文字,并對某些特定的分析模式——比如G. A.柯亨和弗朗哥·莫雷蒂(Franco Moretti)的模式情有獨鐘。另外引人注目的是,您在非常長的一段時間里都用essay(譯作“論說文”或“隨筆”)這種形式來寫作,您最近出版的三本書(《美國外交政策及其智囊》《印度意識形態(tài)》《新的舊世界》)都是在《新左評論》或《倫敦書評》發(fā)表過的論說文的結集。為什么這種形式意義重大?它與您的理論關心有什么關系?
安德森:從來沒人問過我這個。你的問題引發(fā)我思考——我自己并不怎么反思這些事情。我要說的第一點是,我一生的大多數(shù)時間——長達五十年——都在參與期刊(journal)編輯工作。這是我的首要活動。我的主要技能是當編輯。如果你在編一本期刊,那你始終都在處理論說文(essays),或者說文章(articles)。如果你為期刊寫作,你就在寫論說文。因此,某種意義上,這是工作的特性,是我的初始訓練。
在一本期刊的內(nèi)部,總是存在我所謂的“達爾文主義式的空間爭奪”,而這卻是不少作者,尤其是美國作者常常不明白的。每個作者都想在期刊里獲得盡可能多的空間,但并非人人都能有那么多空間,所以你必須在行文上要多簡潔就多簡潔。這是我試圖在《新左評論》制定的一條規(guī)矩:文章不要有重復和冗余。美國社會科學,包括人文學科的文章都有這么一個公式(這是個非常壞的習慣,但愿沒在中國傳染蔓延開來):在文章開頭,你簡要說一下你準備說什么,然后在文章的主體部分,你展開細說,最后,你再重復一遍你剛說過的話。一樣的東西說三遍。讀者一點驚喜也沒有,因為讀者已經(jīng)被提前告知了:“這是我將要說的”,“這是我的結論”。為什么要費勁聽上三遍呢?這是我們無論如何應該避免的習慣。提前的概述、預先的摘要是最不好的,但學術期刊都要求這么做。
然后第二點,你說我偏愛風格清晰和形式簡潔。實際上,在我眼里,這兩種品質(zhì)是相伴相生的,因為如果你有一個清晰的分析,那就意味著,你沒有在論證的時候混進對論證本身來說是次要的很多元素。寫作在形式上應該是簡潔的,因為它在論證上是清晰的。關于風格,你提到某種“特定的分析模式”,還舉了兩個例子。實際上,我并不特別欣賞諸如杰里·柯亨(Jerry Cohen,即G. A.柯亨)的風格,在我看來,他的風格太枯燥、太學究氣(scholastic)了。它很清晰,但不吸引人。與之相對照,我想提兩位意大利作者。兩個人都是我的朋友,他們的寫作既簡潔又明晰,卻都異常雅致:他們是歷史學家卡洛·金茲伯格(Carlo Ginzburg)和文學學者弗朗哥·莫雷蒂。我不會妄圖把我自己和他們?nèi)魏我粋€人相比。金茲伯格具有那種我們稱之為“阿提卡”(Attic)——雅典式——的純潔風格,語言非常簡明、質(zhì)樸,卻又強有力。莫雷蒂雖然是一位出類拔萃的作家,但他的散文的節(jié)奏是口語的節(jié)奏,十分接近于一場生動對話的語言。任何有幸聆聽莫雷蒂講話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極好的老師,而他的寫作風格就擁有他講話時的那些品質(zhì)。我寫的散文幾乎是他的反面。你說它受到了從左到右許多知識分子的褒譽,但實際上,很多人抱怨紛紛,部分原因是我經(jīng)常使用相對罕見、口語中很少使用的拉丁文單詞。少年時,我最崇拜、最喜歡的作者不是我的同時代人,而是十八世紀的作家、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吉本的杰作《羅馬帝國衰亡史》是一部高度正式的、精心反諷之作,我曾將其視為某種絕對的范本,或許我至今仍無意識地受到它的影響。后來,我最欣賞的二十世紀英語作家是偉大的英國小說家安東尼·鮑威爾(Anthony Powell)。他的十二卷系列小說《隨時光之曲起舞》(A Dance to the Music of Time)常常被視為英國最接近普魯斯特的創(chuàng)作。不過,作為一部復雜的敘事,它在許多方面其實是高于普魯斯特的。鮑威爾的寫作之所以與眾不同,部分是因為其中存在大量十七世紀句法和用語的痕跡——我們文學的這一階段最令他著迷。這些不過是我想給你提供的參照,它們或許影響了我自己的風格。
然后你還提了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我寫的論說文和我出版的書之間是什么關系。這里要稍微糾正一下。你說:“您最近出版的三本書都是在《新左評論》或《倫敦書評》發(fā)表過的論說文的結集。”實際上,我從來沒有出過一本僅僅把我在別處已經(jīng)發(fā)過的論說文結集的書。如果我要把我的若干論說文放進一本書里,那么與之前發(fā)過的文章一道,我總會專門為這本書再寫點什么,以便賦予這本書一個如其所是的形式。比如你看《交鋒地帶》(A Zone of Engagement)——顯然這本書沒有被充分地、以一種可以理解的方式翻譯成中文——其中最長的一篇論說文,也就是把福山作為討論起點的《歷史的諸種終結》(The Ends of History,注意是復數(shù)的“終結”),就是為完成這本書而寫的。在《光譜》(Spectrum)中,我希望在左右翼觀念之間有所平衡,但又意識到,我需要再多些中間派的東西,所以我專門為此寫了關于哈貝馬斯的那篇文章(text),就像為了照顧左翼,我也專門寫了關于歷史學家布倫納的一篇。在《新的舊世界》里,關于歐洲一體化理論很長的一章,以及作為結論的、關于歐洲觀念的過去與未來的幾章都是在書里第一次出現(xiàn)。常規(guī)的形式是,如果我決定要把一些論說文放在一起,我就會為此寫些別的東西,以求形成一本連貫一致、內(nèi)里協(xié)調(diào)的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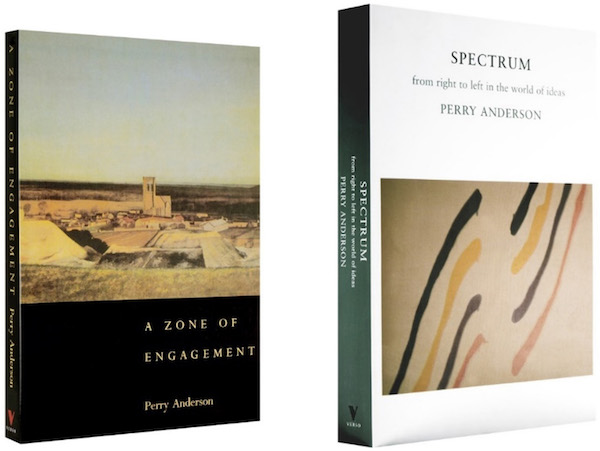
佩里·安德森著:《交鋒地帶》,Verso,1992年5月出版。佩里·安德森著:《光譜》,Verso,2005年11月出版。
我想說的最后一點是最重要的。在英語,以及大多數(shù)的歐洲語言里,論說文(essay)這個術語的邊沿是非常曖昧模糊的。一篇論說文可以是一篇文章,但也可以是一本書。歐洲語言中一些最好的書就被冠以論說文之名——只要想想洛克的《人類理解論》(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就可以了。就我自己而言,相當多的、我出版成書的東西,最初只是一些比較小的計劃,本來只設想為文章,或是其他專書的章節(jié)。我最早的兩本書《從古代到封建主義的過渡》和《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是如此,直到我最近的三本書還是如此。《印度意識形態(tài)》《美國外交政策及其智囊》《霸權的諸次突變》起初都是為一部更大的、關于今天的國與國之間問題的著作而寫的章節(jié),但我寫著寫著,“一章”就寫到了一本書的長度,所以我就把它們作為單獨的書出版了。一篇論說文最終的長度總是無法完全預測的,而這將會決定它是一本書還是一篇文章。所以就我的經(jīng)驗來說,這兩者之間并沒有絕對的(categorical)差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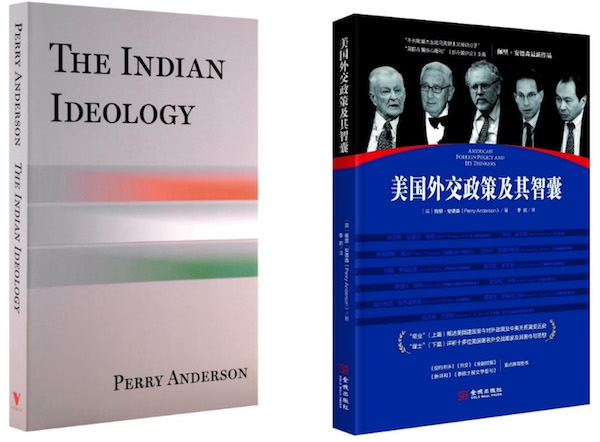
佩里·安德森著:《印度意識形態(tài)》,Verso,2013年10月出版。佩里·安德森著:《美國外交政策及其智囊》,李巖譯,金城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
與風格密切相關的是方法。您對分期(periodization)、分類(categorization)、系統(tǒng)(schematism)方法的嫻熟運用——尤其體現(xiàn)在《國際主義略說》(Internationalism: A Breviary)這樣的文章里——令我印象深刻。在《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的前言,您說您試圖在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經(jīng)驗議題)和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理論問題)之間探索某種中介地帶,同時在“一般”(general)和“特殊”的意義上檢視歐洲的絕對主義。盡管如此,還是有人對您提出了批評,認為您發(fā)展出的只是一個靜態(tài)的社會結構模型,您與E. P.湯普森那場著名的論戰(zhàn)亦與此相關。后來,在《英國馬克思主義的內(nèi)部論爭》(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中,您致力于把湯普森和阿爾都塞的洞見統(tǒng)一在一個框架里。時至今日,您似乎依然堅持著自己的觀點。我想請教,在您的全部著作中,是否存在某種方法上的一致性?
安德森:你的問題里存在對立的兩極(poles)。你引用了我寫《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時的目標,即致力于同時在“一般”與“特殊”的意義上研究歐洲的絕對主義。對我而言,設法把一般的東西和特殊的東西結合起來,是一個方法論的標尺。這意味著:首先建構一個關于你研究對象的一般概念,然后通過觀察特殊案例的異同——也就是在經(jīng)驗領域里比較——來探索、發(fā)展或修改這個概念。當時我對此并沒有想的特別多,但憑借直覺,我努力用這種方式來處理絕對主義的問題。后來,我在一篇論說文里更加明確地這么做了:我原本打算接著寫《絕對主義》的續(xù)篇——資產(chǎn)階級革命,這篇論說文就是在勾勒這個續(xù)篇的輪廓。我對自己早先處理資產(chǎn)階級革命問題的方式非常不滿,愛德華·湯普森批評過那種方式,他的批評無可非議。所以這次我就先從重構資產(chǎn)階級革命這個概念著手,論證馬克思構想它的方式是有缺陷的。一旦資產(chǎn)階級革命的概念經(jīng)過了更加合乎邏輯的重構,你會發(fā)現(xiàn)一個明白易懂的模式浮現(xiàn)了出來——分裂的(divided)歷史個案被分為(dividing)兩種不同類型、不同時期的資產(chǎn)階級革命:這解決了保守主義歷史學家在反復思考相關觀念(notion,其他各處“觀念”,原文均為idea)時所面臨的經(jīng)驗主義困難。如果用歐洲哲學的方式來表達,我當時反對的,是我認為湯普森所代表的東西,即歐洲經(jīng)院哲學術語所謂的唯名論:確信世界上有許多特殊的對象,每個本身都是獨特的(distinct),因此都需要一個與眾不同的名稱。這就是湯普森的名文《英國的獨特性》(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English)的主題。歷史上是英國的東西就是英國本身的東西,決不可以和法國的東西——尤其是法國的東西——相混淆或相比較。我反對這種唯名論立場。但我也同樣反對與它相對立的結構主義立場——歐洲中世紀傳統(tǒng)稱之為“實在論”(realism):這是一種柏拉圖主義的觀念,認為概念作為事物的本質(zhì),具有獨立于其例證的實在(reality)。由此導致的是一整套的抽象化,而沒怎么把握世界的經(jīng)驗多樣性。為了反對這種立場,我會強烈要求我《新左評論》的同事堅持這樣一種口號:你應該永遠記住,任何抽象或一般的論點,唯有在你能為它提供足夠大范圍的實例的時候,才是個好論點。如果你有一個概念或論點,卻沒有很多關于它的好例子,那這個概念或論點就不會很有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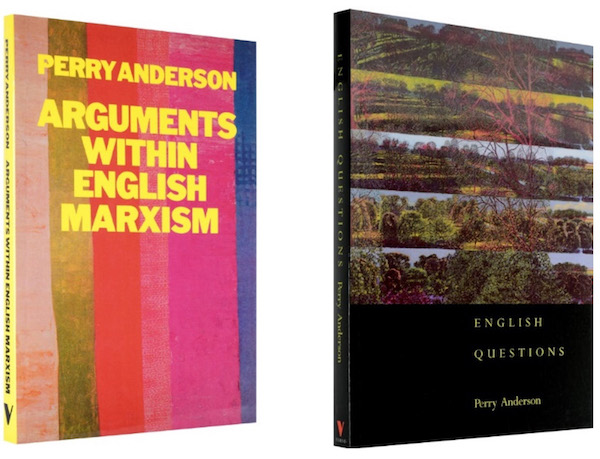
佩里·安德森著:《英國馬克思主義的內(nèi)部論爭》,Verso,1980年4月出版。佩里·安德森著:《英國問題》,Verso,1992年3月出版。
在寫作絕對主義的時候,我覺得我已經(jīng)提出了一個比較令人滿意的框架,可在一般和特殊的意義上同時展開分析。當我轉而寫作二十世紀的歐盟時,我面臨了一個多少有些相似的難題。《新的舊世界》開篇用了三章討論作為整體的歐盟,涵蓋了歐盟的歷史和各種相關理論。然后轉到研究三個處在歐盟核心的大國——德國、法國、意大利,再然后是謀求加入歐盟的大國——土耳其,以及土耳其與一個小歐盟成員國——塞浦路斯——的沖突。其時,我對以下事實感到極為吃驚:百分之九十關于歐盟的著述都是難以置信的乏味、技術化(technical)和缺乏想象力。這些著述充斥著制度的細節(jié),充斥著關于它們的沒完沒了的討論,但那些討論歐盟的專家卻幾乎從不談論組成歐盟的不同成員國的政治、文化。所以,我就想把特殊的國別研究和囊括性的一般結構放在一起。在我看來,結果并不完全令人滿意,即使僅僅是因為我在2009年完成了這本書:而只是自2009年開始,第一次,關于歐洲層面正在發(fā)生的事情的辯論,直接結構了這些國家各自的國內(nèi)政治。在此之前,它們彼此間頗不相干。如今的情況則完全不是這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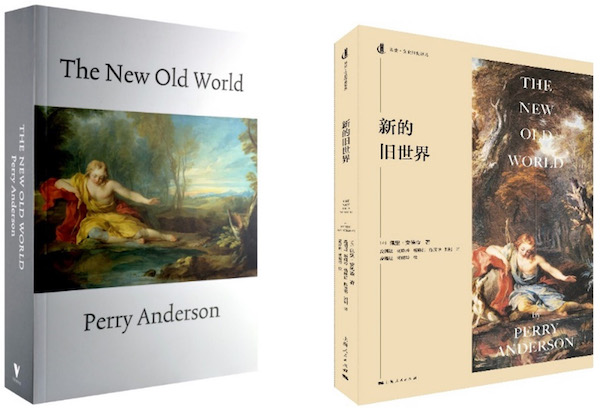
佩里·安德森著:《新的舊世界》,Verso,2009年12月出版。中譯本:上海人民出版社即出。
在我著手下一本書的時候,我想到要以相反的方式開始。在處理當代國家間體系這個問題之前,我會先分別寫組成這個體系的那些重點國家:美國、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以色列等等,詳細考察它們的國內(nèi)政治(社會的結構、政治制度的性質(zhì)、經(jīng)濟的特性)。一旦我完成了這些考察,我就會轉而關注它們之間相互關系的模式。所以先是特殊的,后是一般的,再是二者一道——實際上,就是把學院里兩樣十分隔膜的東西接連起來:一樣是國際關系學的著述,一樣是比較政治學的著述。這兩個領域彼此鮮少聯(lián)系。在美國,有很多很龐大的政治學系,下面有五六個不同的領域:國際關系、國內(nèi)政治、比較政治、政治理論——統(tǒng)統(tǒng)互無干系。
您的寫作中還有另一個關乎風格和方法的突出特征:您大量的書和文章都聚焦于思想的創(chuàng)作者,而非——如您曾經(jīng)坦言的——概念(像以賽亞·伯林那樣)、話語(像昆廷·斯金納那樣)或文本(像雅克·德里達那樣)。比如《安東尼奧·葛蘭西的二律背反》寫葛蘭西,《政治與文學》采訪雷蒙德·威廉斯,《英國馬克思主義的內(nèi)部論爭》寫愛德華·湯普森,《后現(xiàn)代性的起源》寫弗雷德里克·杰姆遜,更不用說《交鋒地帶》及其續(xù)篇《光譜》了(目前的中譯本將后者的書名謬譯成“思想的譜系”),這兩本書幾乎一章寫一位思想家,把“特殊領域的意見資源”存入“政治文化的一般倉庫”里。您為什么要寫人?為什么對您而言,構建一個思想家,或一個時代的總體思想形象如此重要?
安德森:很多因素——智識的、政治的、性情的——都在這里起作用。就智識而言,到了八十年代,我無疑反對其時在西方處于支配地位的處理觀念的方式,即便對那些我可以欣賞的形態(tài)也是如此。伯林作為思想家,有非常吸引人的一面,但總的來說,他以一種非歷史的方式把觀念當成棋子把玩,可以說他不是真正的研究觀念的學者——對此,他本人也有自知之明。德里達對于他從文本中提取的東西常常見解獨到,但是,這一提取本身卻是高度任意的。以斯金納為主要代表的劍橋學派,在這一領域貢獻了比前兩位更有力的成果。但是他們在處理某位作者時,也挑三揀四,只選取自己感興趣的部分討論,而忽略其他部分。劍橋學派最出色的代表、杰出的歷史學家J. G. A.波考克筆下的馬基雅維里,好像只是那個寫了《論李維》的共和主義理論家,而從來沒有寫過《君主論》似的——在另一個聰明的頭腦列奧·施特勞斯那里,情況則恰好相反。斯金納對馬基雅維里的處理相對較少,但問題和波考克一樣。所有這些例子,都對作為整體的一個思想家的著作的總體性(尤其是其中有自相矛盾之處)避而不談。
所以當我著手寫我的論敵愛德華·湯普森,或是構思一本與英國當時的頂尖文化理論家雷蒙德·威廉斯對話的書,我便想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圍內(nèi),把他們的成就作為整體對待。不過這里還有另一個非常強烈的沖動,即我希望把他們傳承給我們的東西,盡可能完整地轉達給我們這一代的左翼。在私人關系上,我同弗雷德里克·杰姆遜更親近,因此關于他的那本書,也多少有些不同:后現(xiàn)代性的概念在杰姆遜那里達到了頂峰(consummation),我試圖圍繞這個頂點,建構關于這一概念的歷史,往復于概念探究與生平考察之間。至于葛蘭西,我僅僅集中在他《獄中札記》里的一個核心的難題性(problematic)——這次不是一個概念,而是概念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nexus),但和杰姆遜的書一樣,我也致力于把這些概念牢牢地落實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之中。這兩本書里我沒有試圖把兩位作者的著作作為整體來重構。

佩里·安德森著:《后現(xiàn)代性的起源》,Verso,1998年7月出版。
不過上述四個例子有著共同的政治意圖,即把一份遺產(chǎn)傳遞給我同時代的左翼,傳遞給那些可能會接著走下去的人們。但另一方面,我寫作后來收進《交鋒地帶》和《光譜》的文章的首要目的則頗為不同。這里,我主要寫的不是左翼思想家,而是中間和右翼的思想家。我確信,1945年以后,典型的左翼文化變得過于內(nèi)向自守了——人們只對左翼觀念感興趣,對那些來自相反陣營、極具原創(chuàng)性的思想家卻漠不關心。我視這種狹隘為貧乏,它只會,如葛蘭西所見,削弱而非強化左翼。一些人認為,只有認同了一個思想家的觀點,才能尊重或欣賞他(或她):這完全是胡說(blind)。這就是為什么我寫了韋伯、伯林、福山、哈耶克、施米特、施特勞斯、奧克肖特:試圖睜開我方的眼睛,去發(fā)現(xiàn)其他方面的財富——同時不妨礙繼續(xù)批評他們。
最后,我還想再補充說一點我關注作者以及他們的作品的原因。今天,在西方——在中國也這樣嗎?——嚴肅的書評實踐正在縮水。如今很普遍的做法是:所謂的書評人把書當作“由頭”,離題萬里,自說自話,對名義上被評的那本書,實際上完全視而不見。《紐約書評》和《倫敦書評》都鼓勵這么做。在我看來,這種做法是麻木不仁的庸俗市儈氣的一種表現(xiàn)形式(a form of callous philistinism)。幾乎很少有哪本書是很容易就寫出來的。把人家辛辛苦苦寫的書——不管你覺得寫得怎么樣——僅僅作為滿足你表現(xiàn)癖,讓你出風頭的借口,這讓我無法接受。就像我經(jīng)常對我的朋友、《倫敦書評》主編瑪麗-凱說的那樣,這就等于你請人到家里來吃晚飯,然后一整晚不跟他說話,甚至看都不看人家一眼。好像有點失禮吧?
一直以來,您都十分關心hegemony(根據(jù)不同語境可譯作“霸權”、“領導權”或“統(tǒng)識”)的問題。在您早期關于英國的論述中,您就使用了這個概念;后來從領導權/霸權的角度,您在《新左評論I》的第一百期(1976)和《新左評論II》的第一百期(2016)分別發(fā)表了關于葛蘭西,以及葛蘭西的繼承人的文章;您2009年和2016年在北京演講的內(nèi)容都與美國霸權有著直接的關系。當我把您的北京演講、您關于喬萬尼·阿瑞吉的討論,以及《美國外交政策及其智囊》的《帝業(yè)》部分結尾段落結合在一起看,我認為您試圖表明的是:雖然美利堅帝國仍舊是今天的霸主(hegemon),但它最終可能失去這一位置,因為(in the sense that)整個霸權/領導權的觀念會在二十一世紀發(fā)生變化。您是這么認為的嗎?此外,您關于二十一世紀的霸權的討論,與哈特、奈格里的“帝國”觀念之間,是否存在某種相似性?——盡管我承認,二者有巨大的差異。

佩里·安德森:《安東尼奧·葛蘭西的二律背反》,載《新左評論I》,第一百期,1976年11/12月。佩里·安德森:《葛蘭西的繼承者》,載《新左評論II》,第一百期,2016年7/8月。
安德森:你這么想是對的:領導權/霸權一直是我寫作的核心主題和關切。事實上,我在2017年春天出版的新書就叫做《這個H詞:霸權的諸次突變》(The H-Word: The Peripeteia of Hegemony)。我們有H彈(H-bomb,即hydrogen bomb,氫彈),也有H詞(H-word,即hegemony,領導權/霸權)。這本書是關于hegemony觀念的各種命運和變異的比較語文學史:從它在古希臘和十九世紀德國的復數(shù)起源,到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交,馬克思主義者在俄國對它的重構,再到葛蘭西在意大利對這些馬克思主義者的遺產(chǎn)的闡發(fā)。然后,我考察了德國保守主義法學家海因里希·特里佩爾(Heinrich Triepel)在第三帝國治下關于霸權的重要著作,考察了冷戰(zhàn)時期在美國和法國的討論對這個概念的影響。在那之后,我們的故事轉到了阿根廷和印度對這個概念的創(chuàng)造性使用。在東亞——中國和日本——從古至今的各種傳統(tǒng)中,這個術語的西方抑揚(inflexions)在霸道和王道的二分中被顛倒:前者強調(diào)的是強制(coercion),后者強調(diào)的是合意(consent)。這本書的最后幾章考察了hegemony觀念在當代的若干用法:比如在清華大學教授國際關系的中國思想家閻學通,以及今天英國、德國和美國的政治思想家和意識形態(tài)宣揚者對它的使用。這本書的企圖是要重建這一十分漫長、復雜而迷人的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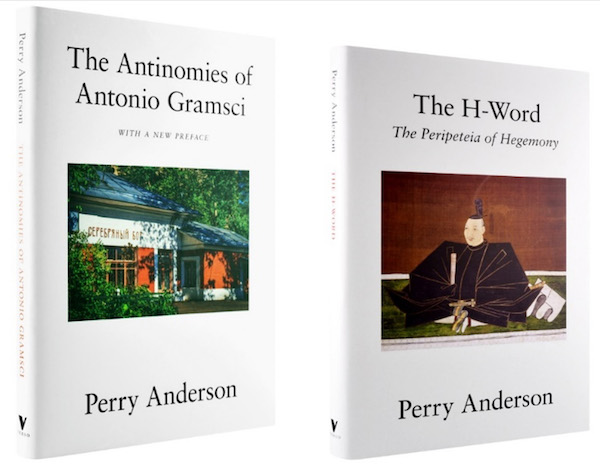
佩里·安德森著:《安東尼奧·葛蘭西的二律背反》,Verso,2017年4月出版。佩里·安德森著:《這個H詞:霸權的諸次突變》,Verso,2017年4月出版。
至于你具體的問題:我是不是認為美利堅帝國今天仍舊是全球霸主,但最終可能失去這一位置,因為整個霸權/領導權的觀念會在二十一世紀經(jīng)歷一場變化?是的,這大致是我的觀點。美利堅合眾國依然是一個具有星球規(guī)模的霸權國家(hegemonic power),但它可能在未必有任何其他勢力(power)取代它的情形下,失去這一位置。你看到一些西方作者明確地,同時一些中國作者隱晦地表達了這樣的看法:中國將成為新的全球霸主。你很可能也知道馬丁·雅克出過一本書叫《當中國統(tǒng)治世界》(注意是“當”,不是“如果”)。我攻擊過這本書,不同意其觀點。不過,可能會出現(xiàn)一個沒有單一霸權國的霸權體系(hegemonic system):在這個體系里,資本主義呈現(xiàn)出自我平衡的內(nèi)穩(wěn)態(tài),它如此普遍,再也不需要一個維穩(wěn)的最高統(tǒng)治者了。這是一種可能發(fā)生的、高度負面的情景(scenario),但絕非完全沒有根據(jù)。
我的立場可以和兩位意大利思想家形成對照。喬萬尼·阿瑞吉在他的《漫長的二十世紀》一書中同樣設想了霸主的逝去,認為美國可能沒有后繼者。但是他設想的那個情景有著非常良性的形態(tài):隨著世界市場社會的到來,資本主義被克服了。顯然,我對如是的結論表示懷疑。你可以在奈格里和哈特的《帝國》一書里發(fā)現(xiàn)同一種視野的另一個變體——對此我持更大程度上的批評態(tài)度。他們認為霸權國已經(jīng)一去不復返了,但這是因為在他們看來,美國——他們眼里的美國一片美好(rosy)——幾乎是人類的一個典范。對他們而言,全世界將要變成某種擴大版本的美國。美國的憲法好得很,是世界上最好的憲法,偉大的美利堅民族完全是文化多元的,是普遍的,因為它有那么豐富的移民。這就是未來。在這個未來中,諸眾會接管一個成了放大版美國的星球。我認為,這完全是妄想。
您的歐洲史著作研究了這樣一個問題:中央集權的絕對主義國家,是如何脫離中世紀封建主義的分裂統(tǒng)治權(parcellized sovereignty)而興起的。由此聯(lián)系中國的歷史,我很容易想到現(xiàn)代中國思想先驅章太炎的話,“歐美日本去封建時代近”,“中國去封建時代遠”,因為中國在很早之前——秦以后——就有了“絕對主義”。類似地,毛澤東晚年論及中國歷史,也有所謂“百代都行秦政法”的說法。不過,您在《兩場革命》里闡釋中國晚近政治史中的古代遺產(chǎn)時,似乎更多地強調(diào)了儒家,而不是——比如說——法家。這里存在脫漏嗎?

佩里·安德森:《兩場革命》,載《新左評論II》,第六十一期,2010年1/2月。
安德森:某種類似于封建主義的東西無疑存在于中國的東周——春秋戰(zhàn)國時代,因為當時的政治主權是高度分散的,形形色色的地方統(tǒng)治者及其臣屬,名義上從大權旁落的君主(residual king)那里獲得土地和頭銜。這比較像封建制度:對周天子(monarchy)懷有殘存的效忠。但中國的古典政治思想里有一個十分驚人的特征,從孔子以來的所有思想家,都毫無例外地認定一個單一統(tǒng)一王國(unified realm)的價值,將其視為根本前提。不論是孟子,還是更現(xiàn)實主義的思想家如荀子都堅信這點。眼下可能是分裂的,但這是件很糟糕的事情。原則上,理想總是要統(tǒng)一(unification)。自從秦朝實現(xiàn)了統(tǒng)一,這個大一統(tǒng)(unity)的前提就成了無條件的前提。分裂確實發(fā)生過,但分裂絕對不可接受,也不會持久。在這個意義上,說秦以后中國沒有任何類似封建主義的東西是對的,反之,你們有一個中央集權的皇帝-官僚制國家。這個國家可能會采取不同的形式——它在宋以前更貴族制一些——但它的基本結構歷朝歷代都沒變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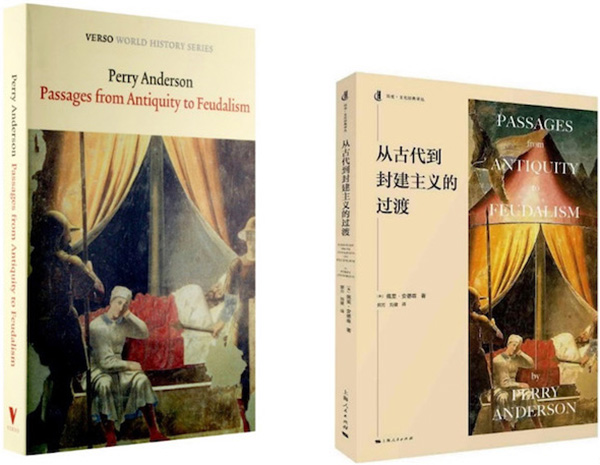
佩里·安德森著:《從古代到封建主義的過渡》,Verso,2013年4月再版。中譯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8月再版。
在我討論絕對主義那本書的后記里,我費了一番功夫對比中國這段歷史和日本歷史。在日本,確實有類似于十分純粹的封建主義形態(tài)的東西,你幾乎可以和歐洲的封建主義逐條對上,盡管,封主和封臣的關系在日本更加不對稱一些。歐洲的封建主義最終產(chǎn)生了集中了封建階級力量的絕對主義國家。在日本,這一轉型從來就沒有完滿實現(xiàn)過。德川幕府是日本前現(xiàn)代時最強大的一元化(unified)統(tǒng)治形式,但它從來沒有演變成一個絕對主義君主政體。它的結構頗為獨特。而這是一個關鍵區(qū)別。我為什么要強調(diào)這點呢?因為那本書最重要的論點之一是:一般而言,與存在于農(nóng)業(yè)(agrarian)官僚帝國(empire)——比如中國——的帝制(imperial state)相比,封建主義提供了一條容易得多,且快得多的通往資本主義的道路。這就是為什么,日本是二十世紀唯一一個多少完全趕上歐洲資本主義的非歐洲社會。我所做的區(qū)分是,日本的封建主義不能像歐洲的封建主義那樣,自發(fā)地、內(nèi)生地實現(xiàn)這一過渡,而它之所以停滯不前,乃是因為它缺少絕對主義轉型。對歐洲的絕對主義轉型而言,一個關鍵的助力來自古代希臘、羅馬的古典遺產(chǎn)。在日本,從中華帝國借來的智識和制度就相當于它的古典遺產(chǎn),但這種助力相較于古希臘、古羅馬要羸弱得多,于是,使明治維新這條通往資本主義的捷徑成為可能,就需要來自西方的外部壓力。這大致是我的觀點。所以我完全同意章太炎的論述起點。

佩里·安德森著:《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Verso,2013年4月再版。中譯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8月再版。
現(xiàn)在我們來談儒法問題。杰出的海外華人學者何炳棣把漢初以來帝制中國的傳統(tǒng)公式用英語總結為:“以儒家緣飾,以法家行事”(ornamentally Confucian, functionally Legalist)——也就是他的版本的“儒表法里”。根據(jù)這個傳統(tǒng)思想,儒家為權力奉獻了裝飾性的外觀,而法家則提供了權力運作的內(nèi)核。我個人認為這過于簡單化了。法家非常關切的是對官員的控制。如果你讀《韓非子》,你會發(fā)現(xiàn),在韓非對秦始皇的先人所建之言、所獻之策中,有相當一部分聚焦于這個難題。群臣百官為所欲為:作為統(tǒng)治者,你怎么能控制住他們?你需要一套規(guī)訓他們的機制。當然,法家也關切對民眾的控制。在這方面,你不能只依賴仁義,你必須有法律——清晰的、毫不含糊的法律:如果誰觸犯了法律,誰就將遭懲罰。但是,如果閱讀文本的話,你會發(fā)現(xiàn)重點更多地落在了控制官員,而非控制民眾上。而儒家不斷發(fā)展——當然,這是在其具有傳奇色彩的創(chuàng)始人久已離去的時代里——則成了法家的反面:在我看來,儒家這種學說的本質(zhì)關切是,如何最好地安民。統(tǒng)治者應該顯示仁義,官員應該務農(nóng)重本,提供小范圍的教育,施行大范圍的教化。當然,與此同時,儒家學說同樣關切如何凝聚文人士大夫,如何在后者當中注入集體精神(ethos)。因此,不論是儒家還是法家,都有這樣的兩個方面,但是這二者在不同學說中所占據(jù)的權重不同。不過,歷史地說,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是,從很早開始,儒家就在國家意識形態(tài)層面取得了徹底的支配權,完敗法家。到南宋,朱熹把四書經(jīng)典化,讓《孟子》成為了某種神圣的文本,而法家傳統(tǒng)則幾乎被禁絕。韓非子變成了所謂被詛咒的作者(auteur maudit)——幾乎不存在一部關于他的像樣的學術評論。直到十八世紀的日本,才第一次有學者敢于為他作注。而在中國,這還要等到十九世紀。意識形態(tài)上,儒家眼里容不得沙子。